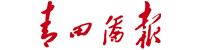(上接11月27日三版)
山不因名而孤,有文则昌。
对于孤山来说,孤不孤都无关重要,只要有了这些历代人文古迹留存就行了,有了这些古迹,孤山就不孤了,就昌盛了,就有灵秀之气了。
至于是谁最先发现孤山,又是哪个南宋人,在这山崖上镌刻下“孤山” 二字,而孤山又是以怎样魅力吸引古代帝王、高僧士子在此营建行宫、御花园、寺庙殿宇和隐居躬耕的,此刻不是我们需要回答或考研的问题。
来此,他们自然有憧憬和幸福。
来此,他们自然有洒脱和安逸。
来此,他们自然有感悟和释怀。
来此,他们自然也有对山水由衷的倾述和眷恋。
但我,不想说他们来此是理想的泯灭,或命运的波折,或情感的跌宕,其实这些都无所谓,反正他们纷至踏来的脚步和有意或无意的举动,却都已经让孤山的文化活了下来,也就是让历史活了下来。
孤山上的每一处古迹,都几乎文风蔚然,尤其是西泠印社、文澜阁、敬一书院、浙江博物馆等;与此山如画的风景相比,而堆积如山的文化和浩瀚经书更是造就“孤山不孤”的原因,令它更闻名遐迩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“孤山寺北贾亭西,水面初平云脚低”早已使孤山名声在外。
北宋著名诗人林逋(和靖)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一传出来,孤山更是惊艳到了江南,那一抹梅花的幽香掠夺了无数人的芳心,带着一颗虔诚、追慕的心一路向西湖寻来,看山、观水、赏风、品梅、画鹤。尽管不知道林和靖归隐孤山的初衷是什么,但是从他的《山园小梅》中已读出了他窖藏着的心态,他的宁静、安逸与淡泊。那时,一定没有什么角逐金银的诱惑,更没有一首小诗寥寥几个字能获十万(甚至几十万)元的诱惑,因而他对孤山的爱才真正我手写我心,现于眼,凝于心,诉于笔。
于是,1000多年过去了,我们依然能够听到历史深处的叙述声——林逋隐居孤山,寄情西湖山水,逍遥自在,栽梅养鹤,终生不仕,也不婚娶,“梅妻鹤子”成了千古传奇,看见他栽的梅从枝头露出傲雪迎春的芳姿,和养的白鹤轻盈起飞的身影,已经形成了西湖的咏叹和落了一地的仙踪。
孤山上梅花仿佛是出尘脱俗的三千美女,在这里一等就是1000多年。1000多年过去了,枝头的千姿百媚还依旧那么楚楚可人,仿佛谁的一声轻唤就会语笑嫣然起来。
走在这里,我们不能不放轻脚步,就是想多沾点梅香和书香。
孤山花木繁茂锦绣,有名的,无名的,一叶一菩提,一花一世界,为这座融自然和人文之美的立体园林赋予山的气息,赐予诗的意境;但它们不识人生的悲欢离合,或浓荫或流翠或嫣红或浅淡或明或暗,疏密有致、参差有序、缤纷烂漫地谋篇布局在溪涧、潭边、泉畔,和前缀后饰在错落别致的亭台楼阁间。你不可小看这些绿树红花,你不知道哪一棵栽于唐代,哪一棵生于宋朝,哪一棵被张祜、苏东坡、白居易、李白、陆游、王安石等人的脚留下过签名,哪一棵曾经被君王移栽过、作为盘景欣赏。
岁月不去管我们的感受,它只是忙着把来过孤山的文人隐士、帝王僧儒们的名字一个个堆积在一起,和把留在孤山上的脍炙人口的佳句与厚重的历史文化传承下来。在这一层层的堆积里,在这一页页的传承中,有枯木逢春,有落花流水,有日月轮回,有名宦贤士,有史书国学,也有西湖的春云秋烟和钱塘江的潮起潮落……但是,我们已找不到那些消逝在尘埃里的枯叶败花和人各自的模样了,他们融汇在一起,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了——史话西湖。
我们无法听到前人的声音,我们也感受不到他们的气息,只有这些“底处凭栏思眇然,孤山塔后阁西偏”“冻木晨闻尾毕浦,孤山景好胜披图”“人间蓬莱是孤山,有梅花处好凭栏”“山外斜阳湖外雪,窗前流水枕前书”“世无遗草真能隐,山有名花转不孤”“断桥荒藓涩,空院落花深”“吴侬生长湖山曲,呼吸湖光饮山渌”“西子拂淡妆,遥岚挂孤镜”“孤山春欲半,犹及见梅花”……诗句的浅唱轻吟,和那些碑文、御印、名家书迹的线条与深痕,真实地告诉我们,他们曾经来过,在这里生活过,他们曾经是孤山和西湖的游客和缔造者,是形象代言人和传播者。
这是一种传承,一种文化的传承,一种历史的传承,也是一种生命的传承。
孤山上的花木告诉我们,在岁月里沉落下去的只是一个躯体而已,一种生命延续的形式,像叶子和花瓣从枝头飘落。但历史与文化还在,文人雅士的灵魂与根脉还在,冬去春来,白雪或暖风又会催醒孤山上的梅花姹紫嫣红。
因而,1000多年后,我们走进孤山赏梅,依旧会感受到古人情感的传递和温暖,1000多年之后,我们该是《山园小梅》的访客了,我们也是书院、印社与文澜阁的读者,我们还应该是作者,要在“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的江南继续写着西湖的故事。
像林逋这样舍弃爱情,不与婚姻,远离尘嚣,孑身隐匿于孤山躬耕农桑和植梅、养鹤, 并以吟诗为乐的人,我们叫他为隐士。而和林逋远避官场与市嚣相比,西湖边首屈一指的名妓苏小小却恰恰相反,爱热闹,装扮得艳媚丹唇,忙碌着穿行于灯红酒绿的舞榭歌台、酒肆青楼间,与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和高官尊爵者觥筹交错,欢颜悦色。好像历代的名人无不被苏小小倾倒(其中也不乏轻薄文人),在历代咏西湖的诗作中,连苏东坡和岳飞都被放在其后:“苏小门前花满枝,苏公堤上女当垆”“苏家弱柳犹含媚,岳墓乔松亦抱忠”……你看看,大诗人白居易都把自己当成苏小小的钦仰者:“若解多情寻小小,绿杨深处是苏家”“苏家小女旧知名,杨柳风前别有情”。而且,在孤山这样一个书圣之地,能为苏小小建墓(慕才亭),使一位歌妓如此体面而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,在中国宗教和道德文化里是前所未有的,也就西湖做了这样一件破例的事情,因缘有点匪夷所思,但颇为深刻。
“和靖高风今已远,后人犹得住孤山”。
时光荏苒,这个在西湖怀抱里的孤山就像一部经典史书,古往今来,应该有许多的读者和观众了。人们从这部史书中能够读出什么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和理解。这座美景和人文融合的孤山,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温暖的道理,一个人的一生总要留下一点什么。未完待续
■ 朱艺伟